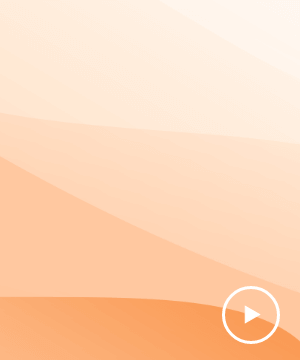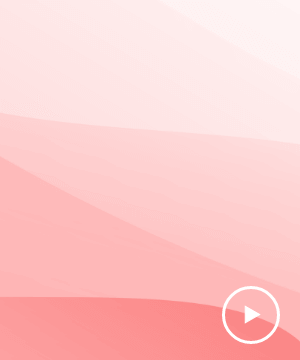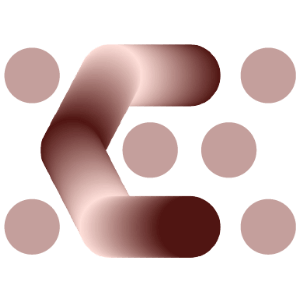義大醫院院長杜元坤是一名充滿矛盾感的「非典型」醫師,他個性豪爽看似大而化之,卻是最精密的神經顯微重建手術國際權威;拉得一手好琴,在高中時拿下全台音樂比賽小提琴組冠軍,但一講到橄欖球運動,馬上「從文人變武將」眼神發亮恨不得馬上衝進運動場;說起音樂與運動的愛好多采多姿,但其實他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奉獻給了醫療,除了除夕跟初一,他每天都在醫院過夜,是名副其實的「住院」院長。
不過,這樣一個「另類」的醫生,其實當初差點就要放棄醫學院改學音樂。杜元坤回憶,功課名列前茅的他一直以為台大醫學院不過是囊中之物,沒想到聯考失常,考到了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,讓他無法超越身為台大校友的父親,也無顏面對「江東父老」。
「當時心情真的跌倒谷底,我踩著腳踏車到台南的安平海邊想自殺,但是騎到海邊覺得肚子好餓,只好摸摸鼻子又騎回去,」到家時早就過了晚餐時間,母親為他煮了一碗麵,杜元坤邊吃邊哭,那頓晚餐至今難以忘懷。
沒想到,到北醫求學一年,杜元坤的生活卻意外的多采多姿,他創立管弦樂團,在圈子內一炮而紅,混得風生水起,從小習琴、師從「台灣小提琴之母」李淑德的他,竟然動了轉學的念頭,考到了師大音樂系。
「原本以為父親會反對,沒想到他竟然說好啊,」杜元坤回憶,但事情當然沒有那麼容易,父親接著說,「轉學就自己付學費,」還沒有經濟能力的杜元坤,只好繼續老實待在北醫。
發明20餘種手術 奠定神經顯微重建手術權威
雖然從來不是典型的好好學生,但是杜元坤對於醫學卻是真的充滿熱情,也確實天賦異稟。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李祖德便形容,第一次和杜元坤打交道的人,十之八九會被他那豪邁而不拘小節的個性深深吸引,並打從心裡懷疑:他真的是個能做全球最精細手術的醫師嗎?
他雖是骨科醫師,卻不甘於依循傳統只繞著骨頭做些敲敲打打的工作,還跨界去做臂神經叢繞道移植手術、皮瓣移植顯微手術以及脊椎重建手術這些整形外科、神經外科醫師專攻的術式,甚至在這些領域發明了20多種手術方式。
「癱瘓者的神經斷了,在原地硬要重新打通神經是不可能的,」杜元坤解釋,但是就像告訴公路坍方了,可以改走省道,杜元坤將神經繞道,成功解決了手術的瓶頸,將這類型的癱瘓手術成功率,從原先的10-20%,提升到85-90%。
1995年,杜元坤的父親因為糖尿病惡化需要截肢,幫自己最親近的人動手術往往是最困難的,許多醫生怕親情影響專業表現,會選擇將家人轉給自己的老師,或是請老師陪同開刀,但是杜元坤說:「我開所有人的刀,都是當親人在開,所以並沒有差別。」
他決定以自創術式,將左大腿的血管接到右大腿的膝蓋,再從膝蓋接到腳,成功保住了父親的腳,父親欣慰地說:「花那麼多錢送你學醫,總算值得了。」這種手術後來被稱為「梅約術式」,後來在梅約醫學中心發揚光大。
全台最愛橄欖球的骨科醫生
認識杜元坤的人都知道,他是出了名的橄欖球狂熱者,杜元坤自醫學院結識的好友雙和醫院院長吳麥斯便提到,兩人一起闖蕩的青春年少,有不少時光都是在橄欖球場度過的。
一直到現在,杜元坤的辦公室滿是橄欖球球具、球衣,這項運動是他最熱愛的休閒活動。甚至,身為全台最迷橄欖球的骨科醫師,台灣有8成橄欖球選手的骨折手術,都是由杜元坤執刀的,「因為我也是運動員,最清楚這些選手的身體情況。」
打過那麼多場球賽、為眾多運動員執刀,「橄欖球是個高危險的球類運動」,這一點,熱衷於此的杜元坤比誰都清楚,他全身上上下下因橄欖球造成的骨折、傷疤多到難以計算。
「你看我頭上這個凹洞,」杜元坤指著頭頂,「這是被對方球員釘鞋一腳踩下去的,當時馬上昏倒,送到醫院醒來第一句話是『我在哪?我還要上場!』」甚至,杜元坤年少時在橄欖球場上的好友,就因為熱身不徹底,不幸頸椎斷掉,當場癱瘓,幾天後就離世了。
「打橄欖球確實是個不太理性的行為,」杜元坤笑笑坦承,前幾年他上場打球卻骨折,這才發現真的有些年紀了,不過這個貫徹一生的熱情,卻也不是說放下就放下,「人嘛,總是有一些『壞』嗜好。」
給未來醫師的忠告:別忘了病人第一 終身學習
去年杜元坤的兒子考上了台大醫科,也是感受到了父親對於這個行業的熱情,「他個性跟我一樣很臭屁,」杜元坤大笑,透露兒子以後想走神經外科。
就像橄欖球這個嗜好,杜元坤建議這些年輕醫界學子,找到一件能夠帶給自己長期收益和幸福感的事,把它排進每天的日程中。這將幫助我們對抗庸常、平凡、索然無味的日常生活,讓我們不斷保持頭腦清醒。
像是大學社團活動,校際之間的交流聯誼、體育活動、休閒活動,甚至偏遠的山地離島義診服務,這些都會讓自己成長,頭腦清醒,並且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對於想要選擇骨科的醫生,杜元坤建議可以用個性來選擇方向:「外向活潑的可以選擇關節重建、運動醫學;謹慎含蓄的不妨考慮小兒骨科、脊椎骨科,」而杜元坤自己最擅長的神經纖維外科方向,他點出了「紀律、創新」等特質。
「想要當一個好醫生,一定要堅持好的訓練,記得終身學習,病人第一,永遠要有奉獻的精神,」杜元坤指出,「身為醫生,最大的成就就是救人。」
延伸閱讀:
文/林以璿 圖/許嘉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