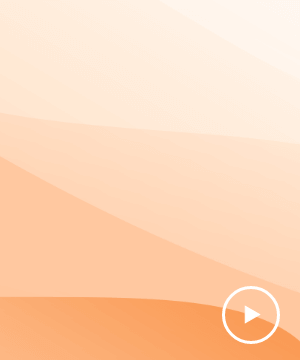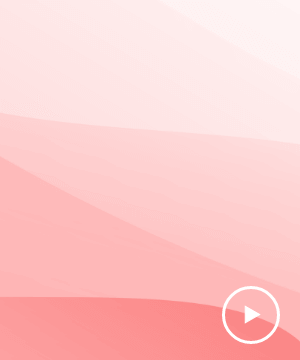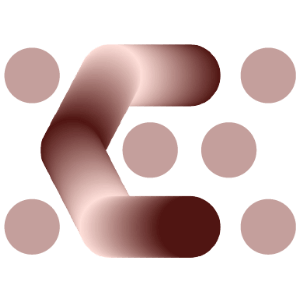在回家途中迷路、開車開到田裡,林添發被確診失智症的時候智力只有7歲,但不服輸的他決定要把握珍貴的美好生命、重新回到學校唸書,還在今年拿下了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的碩士學位,「我並不把自己當病人。」
失智症還有迴轉的機會
過去談論到「失智症」,大家第一個反應都是「這是不能挽回」的疾病,在失智症電影《我想念我自己》中,茱莉安・摩爾還有一句經典台詞,「我寧願我得到的是癌症,而不是失智症。」讓失智症蒙上了更深的陰影。
但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請來導演劉臣恩,將3位確診失智年數分別是17、5、2年的患者故事拍成《與失智共舞》的短片,結果發現他們不只擋住了失智帶來的退化,甚至還進步了。社工主任陳俊佑說,台灣有27萬失智症患者,其中有18萬是輕度,如果可以早點治療,其實後期面對的重度失能,是可以堵住的。

台大醫學院職能治療系副教授毛慧芬說,其實在很多研究中都發現,用改變生活形態的方式,的確可以延緩、甚至改善失智症的狀況;國外有芬蘭著名的「FINGER」研究,讓1260位有輕度認知障礙的老人分成2組,一組接受全方位的生活形態改變,一組只給建議,2年之後,改變生活形態的那組思維、訊息處理的認知功能提升了80%。
「生活形態不只有健康飲食、運動而已,還有動腦的運動、跟人相處的機會。」毛慧芬說,像是3位患者分別用了學書法、教日文,規劃活動,跳舞等方式,讓腦部接受到多元刺激,反而能把退化的腦部再活化。
從7歲智力到碩士學歷
「我想打電話,拿起電話嘟嘟嘟⋯⋯就愣在那邊,因為看著電話簿怎麼也看不清楚號碼,也撥不出去。」現在91歲的林添發確診失智症已經有17年,一開始只是無法打電話,後來一天到晚想睡覺,開車想睡、等紅燈也想睡,有次亂開還掉進田裡,甚至看著滿屋子的兒子、媳婦、孫子,竟然連他們的名字都說不出來。
73歲時,林添發確診失智症,而且醫師宣布智力只剩下7歲。「要我怎麼辦?我也很無奈啊!」但是他意外發現,自己雖然忘記中文、台語,還可以記得日語,所以他毅然決定在社區教日語、也開始上太極拳的課程,沒想到每天忙著備課、運動,忘記自己是病人,竟然連失智的症狀都漸漸好了。
而林添發受到鼓勵,一不做二不休,成立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嘉義大林志工站,從照顧12位獨居老人,一直到現在服務了200多位老人,還受到日本讀賣新聞、公視特派員報導「老老照顧」;更決定到南華大學進修,先拿了大學學歷、又在今年拿到碩士學歷,而且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就可以自己搭公車上下學、不會迷路。
「爸爸很堅毅,所以我們願意陪著他一起做他想做的事情。」林添發的媳婦說,「真的不要緊張,我自己也在醫療機構工作20多年,看過很多,最緊張的通常都是家人,但病人要好,首先家人要放下,很多時候都是家人放不下。」
連痲瘋病人我都不怕,失智有什麼好怕的?
今年71歲的劉仁海是一位牧師,在多年前因為要籌措興建養護中心的經費,壓力太大而中風,「我就知道我是失智的高危險群,因為中風的位置在腦幹,我沒有眼歪嘴斜,但我失智的風險很高。」
結果在2014年,劉仁海果然確診失智症,當下他自己雖然平靜,太太楊菊鳳卻說自己「完全不能接受」。「他來接我的時候,從早上8點、9點、10點一直繞到下午1點,才告訴我說他找不到停車位。我那時就知道不對勁,後來確診,生活上大小事都要重複問,啊我的這個在哪裡、那個在哪裡,而且情緒變得很敏感,以前從來不會這樣的,我只能說我不能接受。」
2個人在一開始的摩擦很多,但劉仁海還是一如既往的到處忙碌。「以前我曾經帶學生去樂生療養院照顧過痲瘋病人,而我擁抱過這麼多痲瘋病人,都沒有被傳染,失智症我有什麼好怕的呢?」

當然對楊菊鳳來說,劉仁海現在講話有時還是「令人生氣」,但已經越來越進步、自己也可以慢慢調適了。而劉仁海現在還兼任幾個基金會的董事長或理事,「其實失智就像感冒流鼻水,一定會有不舒服,但我不讓自己的生活縮減,我用腦過日子,行程滿滿滿,根本不用怕。」
好姐妹把我從迷路裡抓回來
照顧失智媽媽5年的白婉芝原本是小學老師兼出納組長,18歲就考上正式老師的她把戲劇納入課程設計,獲得許多優良教師的獎項,這也讓她對自己充滿信心,所以一開始發現失智的時候,看著原本熟悉的五線譜、帳簿,根本不能相信自己完全看不懂,「怎麼可能,我這麼聰明,怎麼會告訴我這些我都忘了、不會了?」
無奈確診失智症之後,已經70歲的白婉芝看著90歲的媽媽,就好像看著自己的未來,「有半年我都把自己關在家裡,就是不能接受。」但在家裡她也時常打翻東西,或是看著東西不知道那是什麼,生活上也有許多困擾。而媽媽的狀況也越來越差,有次半夜在廁所跌倒,2個人只能在廁所枯坐一整個晚上,考慮到自己的狀況,她最後還是決定把媽媽送到安養院。
不過在無助的時候,白婉芝在自家陽台上看到隔壁有一群人在開心的上舞蹈課,心裡很羨慕,看著看著,忍不住「呼嚕呼嚕的跑進去」,於是認識了一群好姐妹,甚至還互相「結拜」;因為失智的關係,有時候白婉芝會迷路、找不到她們,「但她們始終把我帶在身邊,每星期還到我家煮飯給我吃。」

在她們的鼓勵下,白婉芝開始接觸茶道、日本舞蹈,甚至還去分享跟表演,她也養成記筆記的習慣,把所有要記住的東西全部寫下來,貼在牆上、日曆上,跟自己的生命搶時間。「我也跟姐妹們說好了,如果我不在,星期幾誰要去看我媽媽都排好了,我有了朋友,就不覺得生命會是痛苦的。」
延伸閱讀
文/盧映慈 圖/許嘉真